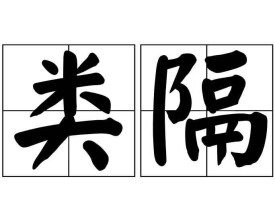類隔
音韻學術語
音韻學術語。凡反切上字與所切之字有重唇﹑輕唇或舌頭﹑舌上之異,叫做"類隔切"。隔者隔礙之謂,二者聲不同類。故名。然古人制反切,皆取"音和",如"篇,芳連切","篇"屬重唇音"滂"p〔p'〕母,"芳"屬輕唇音"敷"〔f'〕母。其實古無輕唇和舌上音,"篇"和"芳"都是"滂"母。唐宋人不知古音,謂之"類隔",蓋出於誤會。

相關書籍
學術研究的方法、結論是從材料產生的。音韻學的材料不幸有殘缺的,有什麼樣的材料,就有什麼樣的方法和結論。底下以材料為綱,把過去研究家採用的方法舉例講出來。也就是介紹音韻研究“做什麼”、“怎麼做”。這兩樣講明白了,音韻學“是什麼”也就不言而喻了。最後說說音韻學發展的簡史。
各民族在史前或有史的早期,即便沒有文字,就有史詩了。這些史詩多數有半專業的人演唱或是念。和史詩同時或稍後又產生了抒情的民間小詩。有些詩可能押韻,漢族的最早的詩就大部是押韻的。最早結成集的就是《詩經》。
先民多半迷信。有的故事,包括一部分史實;都在算卦的卦辭里保存著。這種卦辭也大半押韻,保存在《易經》里。
在開始結集的時候,這些押韻絕大多數是好聽、順口的。年代久了,語音變了,就有些地方不順口了。比方《詩經》的第一首《關睢》第一章的 1、2、4句末字是“鳩”、“洲”、“逑”,很順口,第三章的1、2、4句末字是"得"、"服"、"側",就不那麼順口了。這時候就有人出來研究。研究的結果,認為現代讀音"服"念【-u夿】類音是錯了,應當念【b媅夿】。出錯兒由誰負責呢?由唐朝官方承認的《切韻》和它的修訂本《唐韻》負責,因為他們把“服”和讀“族”“屋"的字收在一韻。用這個觀點寫成書的,就有顧炎武的《唐韻正》。雖然他也有所承受,不過他是第一個作得詳盡的。有單討論古四聲的,就象江有誥的《唐韻四聲正》。體例都是先列一個字,再說明“唐韻”注音怎麼“錯”了。
根據“正”的結果,有人把許多古書用來押韻的字標出來,有的加上自己認為對的音注。這麼作的有顧炎武的《詩本音》等等。直到現在,還有人繼續作。
“正”了以後,把幾千常用字分成多少類,或者叫“部”。作法常是列十幾個格子,每個格子里寫上本部包括《廣韻》的哪幾個韻。這樣,除零星的例外字以外,大多數字該歸入什麼部就一目了然了。這種工作就叫分部的工作。如段玉裁的《六書音均表》一。為表示根據充足,還有單把入韻字列成譜的。例如《六書音均表》四。
從整理單個韻腳字到分部在方法上是跨進了一步:自然科學的方法總是從個體審查到分類的。不過韻腳字分類和自然界的動植物分類有些不同的地方:實例太少,使分類的界限不清。清代人給“陽唐”部【-ɑ嬜、 -iɑ嬜】分類界限相當清楚,例外不多。因為這個部字數多,押韻就容易遵守比較嚴格的規矩,提起“閉口九韻”(即現代粵、客、閩南文讀里用【-m】收尾的部)來,因為字少,詩人們就往往漫出分部的界限──內容和形式有矛盾,內容總是衝破形式。把這九韻里哪些字分成兩部,清代人從來沒有統一的結論。段玉裁《答江晉三論韻》說:“九韻古人用者絕少,既難識別;其可分者,又犬牙錯出,莫辨賓主:可勿論其短長也。”就反映了這個情況。這是材料少帶來的先天缺陷。
有人不贊成或不完全贊成合韻這個提法,就說某些字從原來的甲部流進乙部去了。從部說, 這叫“通”;從字說,就叫“轉”。講“通轉”是因為材料是漢字,和拼音文字里說句“a變成e”那麼清楚的話比起來,困難得多,所以始終沒有明確的定義。從戴震開始講“相配互轉”、“鄰近遞轉”到孔廣森(1752~1786)“陰陽對轉”,再到章炳麟、《成均圖》的"對轉"、"旁轉"、 ……六種“轉”算髮展到頂點了。
以上提到的人和著作都把注意力集中到《 詩 》上,《易》、《楚辭》就擺在次要的位置。後代人學會“分部”、“合韻”或“通轉”兩種方法,有人把它們應用來講漢魏六朝詩賦的韻。羅常培、周祖謨就曾經列過這種譜。至於給唐詩、宋詞列譜的人就多了。
《說文解字》收了9000多字,80%是諧聲字,比方“工”字北京音念gong,韻是-ong。從“工”聲,也就是說用"工"作主諧字來表示全字讀音的有功、攻、紅、空、邛、汞、貢、……後頭全有-ong這樣的音。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說:“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這麼一來,研究諧聲字可以用不到700個字作代表,正好象用一個“工”代表“功”等7個以上的字一樣。雖然諧聲字大量產生的年代,開始比《詩》、《易》早些,結尾晚得多,但是它們的音分起類來跟《詩》韻大致相合,所以有人把主諧字(像上文的“工”)列成表來和韻譜印證。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二就是。
"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只是說大勢。“求”在《說文》是象形字,畫了一件皮襖。“裘”只是加了個偏旁。可是“求”在“尤幽”部,“裘”在“之咍”部。換句話說,諧聲里也不真能“萬字而必同部”,也有“通轉”。所以嚴可均書後頭有個十六部《聲類出入表》。結果幾乎沒有一個部不跟另一個部有通轉關係。
一部書傳抄久了,不能保證一字不走樣。秦始皇燒書,《詩》因為好背,漢初就又流行了。離燒書時間不過十幾二十年。可是就有齊、魯、韓三家,字句不完全一樣。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寫石經,《公羊春秋》碑後有"顏氏言……"等字樣,記下異文。世傳《春秋經》三家文字就有差異。左氏《經》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金文作“鼄”,《公羊》作“邾婁”。看來這個地名在《公羊》家是念【*tro】一類音。清代錢大昕利用古書異文證明古代沒有某幾個聲母,比方《詩·邶·谷風》“匍匐救之”,《禮記·檀弓》引作“扶服”,結論說“古無奉紐”,擴大了說“古無輕唇”。這些異文里多數可以反映先秦兩漢文字通借的情況,間接反映古代一些語音情況。《左傳》昭公十五年“費無極”,《漢書·古今人表》作“費亡極”:這就是“魚陽對轉”的好例子,可以給講“通轉”的人提供旁證。清代人用得多。不過異文有起得比較晚的。不都可靠。
漢代人給經書作注,經常用“×讀若×”;“×讀如×”。從字面看,“若”只能翻成現代話“像”。至於像到什麼程度,那沒法子肯定。有些“讀若”簡直暗示某個字是錯字,該改成另一個字。《周禮·大卜》:“三曰‘咸陟’”,鄭玄(127~200)說:“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這就是等於把“陟”改成“德”。“德”是從“得”派生的詞。
另外,說“若”不過是“像”,有人拿他來講古韻分部,也不周全,還得加上不少講“通轉”的話。
除“讀若”以外,還有《公羊》何休(129~182)注的“長言”、“短言”、“內而深”、“外而淺”,高誘(東漢人,生卒不詳)注《淮南子》的“急氣言”、“緩氣言”等等,都因為材料太少,下定義各家意見不一,也沒什麼人利用。
《易·說卦》說:“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兌,說也。”這裡訓釋字和被訓釋字聲音非常近。可能一個是通語、一個是行業語,或是兩個詞是同源詞。後代的研究者發現每一對字音近,就起個名字叫“聲訓”。《說卦》大約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是創始的。《書·堯典》:“在璇璣玉衡。”伏生《大傳》說:“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已經用聲訓了。伏生從秦活到漢。漢代人大大發展了這種註釋法。到《白虎通》達到極盛。漢末劉熙、《釋名》就寫成專書了。過去講古韻的人常用聲訓作古韻分部的輔助材料。清代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作的比較詳細。利用聲訓研究聲母的人比較少。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曾利用《釋名》“天顯也”證明“天竺”譯的是古波斯文Hindu,等於梵文Sindhu“身毒”。
反切出現,最早在漢末。歷來相傳是孫炎開始作的。章炳麟《國故論衡·音理論》說:“……是應劭時已有反語。”日本釋安然《悉曇藏》一引《韻詮·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誥定。”看起來反切是東漢末創始的。有了反切,漢族人才有了比較準確的注音方法。
如果有人為上千個字作了反切,人們就可以推測出來他的聲韻有多少類。推測用系聯的方法。這是清末陳澧創始的。這裡又分 3種情況:①同用:冬都 宗 切、當都郎切同用“都”字,所以“冬”、“當”是一類。②互用:當都朗切、都當孤切兩個字互用,所以是一類。③遞用:冬都 宗 切、都當孤切原則是后一個字給前一個字作切,再后一個字又給第二個字作切,所以這一串字是一類。
除此以外,還有反證法。比如《廣韻》支韻媯居為切、規居隨切。既然切上字同類,那麼“為”、“隨”韻不同類。
靠這些方法,再加上別的一些補充手段,人們有研究專人專書用的反切上下字的。現代人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可以算最早的這類著作。
有人把上萬個常用字分成若干組,每組裡的字音相同,在前頭加一個○,在第一個字底下註上反切,若干組音節後半發音相同,放到一處就叫一個“韻”。每韻用第一個字作代表,比方所有某些組後半發-ong音的字抄到一起,用第一個字“東”作代表,就叫東韻。若干個韻總結集成一部書,就叫韻書。
現存最有權威的韻書是隋代陸法言的《切韻》,本書殘缺,有幾種增修本,最通行的是宋代修的《廣韻》。拿《廣韻》作《切韻》的代表,用系聯法推求它的聲類韻類的第一個人是陳澧。他著有《切韻考》內、外篇。從“照穿床審禪”里分出“庄初神山”,讓流行的“正齒”音分成兩組,從“喻”里分出“於”,讓三四等分開,都是他創始的。把“支、脂、……”等韻分成三、四類,讓人們注意到“重紐”現象也是他的貢獻。
從漢末到隋,作反切的人也有不完全一致的。這是時間地域的不同造成的。《廣韻》“卑”字“府移切”,在現代大多數方言里可能切出一個像“飛”字的音。宋代修《廣韻》,每卷後頭就加一行“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第一個字就是“卑必移切”。所謂“類隔”是說兩類切上字歷史上來源相近,互相代用。“音和”是類隔的反面,也就是正常的反切。有人就利用這種“類隔”反切作線索,加上別的材料,證明在古音里這兩類不分。錢大昕《古無輕唇》、《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兩篇文章就是出名的開創工作。研究古韻的越分越細,研究古紐的越並越少。這是材料方法造成的,未必十足反映真相。
反切的方法是用切上字的聲母,切下字的韻母合成一個新音節。有時候切上切下字連著念恰好就是要切的新音節,像“雍”用“於用”作切,只是偶然碰巧了。有一種改良者,想把一切切上字都改用 -e、-i、-u、-ü收尾的,一切切下字都用零聲母字,讓反切變成連讀。這種人用心很好,效果可不好。明呂坤(1536~1618)的《交泰韻》就是這麼作的。結果為符合上頭的兩個條件,像“空屋”切“酷”那樣的例不易多得,就不得不找好多怪字來作切上下字。比方用“?翁”給“終”字注音就是。改良方法是歷史語音學方法論範圍里的東西。
用同一種書的不同本子互相校勘,也是音韻學的輔助部門。用古今兩種以上韻書比較,是語音演變史的準備工作。陳澧就把這兩種工作全作過。
從先秦起,漢族人就曾經和外國接觸,試著記下他們的地名, 族(國)名。《山海經·海內經》里有“天毒”,就是Hindu,《史記·大宛傳》的“身毒”,今天的印度。漢武帝時候的“匈奴”,梵文叫Hū╯a。這些最早是口頭相傳。到東漢明帝時,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駝經,來到洛陽,出《四十二章經》,裡頭就開始出現像“阿羅漢” (梵文arhan)那樣的對音。到初唐,密教盛行,需要對譯大段的咒語,對音事業大大興旺起來了。古代“念”佛是一心想念佛。密教念佛,是大段的背梵文咒。咒靠漢字寫。後人研究哪些梵文音用什麼漢字記,是研究當時漢字讀音的捷徑。另外唐初漢藏王室通婚,立碑結盟,有一大批人名、官名,是雙語的。這種對音材料也是極有用的。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就是利用梵漢藏漢對音研究作成的。
從武則天時代起,密教大量流行。密教摻雜著巫術,得大量念咒;咒音不準,引來惡果。人們就開始學悉曇。悉曇就是梵文的識字發音的入門讀本,包括字母、拼讀、連音規矩等等。漢族和尚學了它,得到分析語音的能力和術語。他們也利用這些知識分析漢語語音。最早的嘗試是分出漢語的開頭輔音。明呂維祺(1587~1641)《同文鐸》說:“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后溫首座(守溫)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是為三十六母。”叫"大唐舍利"可能為的是和日本著名尼僧"舍利"分開。但是歷代高僧傳里不見大唐舍利。敦煌出的"南梁漢比丘"《守溫字母》殘卷里可只有30個字母。可見早期和尚們是比照梵文來分析漢語的聲母的。一是創造了三十六字母,並按發音部位把它們分成“喉牙舌齒唇”,每一個部位又按發音聲帶顫動不顫動分出“清、次清、濁、清濁”四個大類。二是把韻母分為開合兩類和四個等,分開合這一點顯然是漢族創造的。梵文悉曇章橫行以ɑ、ā、i、ī等14個母音為次序排,和它們拼的字母寫成豎行,按k、kh、ɡ等33個輔音分組排,粗分類可以說按發音部位排。中國和尚是把悉曇章轉了一個順時針90°角,橫行是喉牙舌齒唇,豎行是一個(分平上去入)或一組韻。這樣,就列出早期的音節總表來了,那就是等韻圖。研究者從這種圖表出發,對《切韻》和當時的語音能夠有比較明確和細緻的了解。
宋代人開始允許“××同用”,和尚們因此也敢大膽歸併。安然《悉曇藏》二說:“又如真旦《韻詮》五十韻頭,今於天竺悉曇十六韻頭皆悉攝盡,更無遺余;以彼羅盧何反家古牙反攝此阿、阿引……。"和尚們歸併漢語韻成十六攝 (parigraha)是從武周開始的,為唐音分類提供了線索。凡在一攝里的韻彼此相像,後來有些書乾脆就合併。
語音變了,韻圖也逐漸隨著變。到了明清的時候,有些人就大刀闊斧地描寫方音,像《戚林八音》就是。到這個階段,等韻就完全擺脫了《切韻》的舊框框,人們研究它們,寧可說把它作為研究近古通語或方音的材料。現代人陶燠民《閩音研究》就藉助於《八音》。再底下的學者就受東西洋影響試擬新字母了。
從讀若到反切,是在記音技術上一大進步。可是舉個最好認的字來說明某個難字的音和它相等或相似這種方法也方便。《廣韻》“拯”字注說“無韻切,音蒸上聲”(故宮本王仁昫《切韻》字跡模糊,似亦即此語)就是個好例。因為這個韻里別的字全是怪字。這可以說明直音還有它的作用。唐代唐玄度作《九經字樣》說:“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他注音“‘刊’,音‘渴平’”,就是利用講四聲八病的文藝理論家“刊、侃、看、渴”是“正紐”(兩句里用兩個同紐的字就算文病),倒過來給“刊”字注音。其餘古注像東晉郭璞《山海經南山經》注說:"?,音幾。"早就有了。
碰上一組字同音,裡頭只有兩個常用,直音就遇上困難。用難字幫不了讀者的忙,用不十分常用的字常遇上“甲音乙”、“乙音甲”這類循環注音的例子。
近兩個世紀,西歐北美的人跟漢族往來,從漢語借過去一些詞。漢族是喝茶的發明者,別的民族就一面學這種習慣,一面學這個話。北方人茶念chá,俄羅斯人就學會說чай,日本人說チャ。南方出口茶的地方是廈門。廈門人茶念【te1】,荷蘭人學說tee,英吉利人學說tea。從這裡可以推測某一個時代漢語某些方言的個別字音。
這方面的研究,搜集資料的有趙元任《廣西傜歌記音》,分量很大。研究成果還比較零星。
這種研究總跟民族交通史交叉。這種資料也是“古已有之”了。梵文里稱中國為“支那”cīna,印度古史詩《摩訶波羅多》里已經有了,不過很零星。
漢族人和別的民族一樣,也有利用語言來尋開心的習慣。在意義方面有雙關一類手法,在語言方面就有用"愚魏衰收"來嘲笑魏收的體語,也有“……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的事(《世說新語》)。到現代有利用反切原理造隱語的切口,有歇後語里利用同音詞的,像“外甥打燈籠──照舅”那類,可以作證明古代不同音的字“舅”、“舊”在現代北京話念得一樣的例證。這些材料零散,也可以作研究音韻的輔助材料。
現代方言絕大多數是從南北朝的音演變下來的。北齊顏之推在《家訓·音辭》里評論各地方音,認為最淳正的數金陵和洛下兩處。現代方言,除閩方言以外,都可以用《切韻》作起點講它的演變。即便是閩方言,特別是閩南話白話音,雖然缺舌上,輕唇兩組音,卻並沒出《切韻》的範圍,更沒出錢大昕學說(見古紐)的範圍。閩南“老”字有上、濁去兩種音。前者跟一切“官話”、粵等方言相合,後者正是“濁上變去”的好例,這是在唐代已經發生的現象。國內的學者從來沒懷疑過:現代漢語方言包括閩方言都跟《切韻》音系有著直接或間接的歷史淵源關係。調查明白了現代方言,可以倒推出來《切韻》的面目的輪廓。當然這種擬構法有缺點:瞄準差一點兒,中靶差幾尺。擬構出來,免不了有些不著邊際的成分在裡頭。這得靠別的材料來校正。只要不斷進行修正,最後還是能夠獲得比較正確的結論的。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就是利用這種方法的好例。
此外像利用漢語和同系語如藏語的詞音比較來推測古漢語語音等新興邊緣學科,都還在萌芽狀態,不詳述。
回顧音韻學發展的歷史,那道路好像閃電一樣曲折。大致看它的主流,可以粗略地分為4期。當然,這些期是互相交錯的。
第1期從漢代起到宋代為止。這一期的成就主要是有人發現了一種析音的方法,比如說漢末人發明了反切,用來給漢字注音。這件工作本身是語音學的工作,並不是歷史語音學。不過給歷史語音學儲備了資料。又比如從呂靜作《韻集》,開始把字按音分類,引起了夏侯?(原作該)等人仿效,寫了《韻略》等書,直到陸法言《切韻》出現,在漢族的語言研究里出現了詳盡的韻書,成為中國語言學里獨有的音序語素典。在析音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但是工作也是斷代描寫,記錄資料性質。又比如唐五代僧徒討論用哪些漢字對哪些梵文音合適,從玄奘《大唐西域記》里批評舊譯訛、略的話起,直到五代正式訂出字母,隨後比照印度《悉曇章》造出等韻圖,列出那個時代的音節總表。這一來使漢族有了比較語音學的雛型。功勞是大的。不過也只限於斷代,仍舊是資料性質。
另一面,也有顏之推等人在陸法言家討論“古今是非,古今通塞”,顏著《家訓》評論古韻書。又比如陸德明在《詩·燕燕》的《音義》里說:“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 。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方面引了最早講叶音的話,一方面對他的任意性表示反對,作出解釋。這些才是真正的歷史語音學。第一期可以叫“萌芽期”。
第2期大致可以說從宋代就開始了。宋代吳棫採用叶音說,後人不從。但是他卻開始給古韻粗粗的分部。經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提倡,清代顧炎武發揚光大,古韻學才走上科學化的路。一方面排斥了叶音說的任意性,一方面建立了古今音不同的史的概念。音韻學才脫離了偶發的階段,進入了正式研究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學者原始的動機是求給《詩經》、《楚辭》的韻腳定出順口、悅耳的念法來。這是“通經”的工作。另外,顧炎武希望從語音復古喚起漢族人的民族意識來,未免迂曲少功。但是這也是“致用”的工作的一種內容。到段玉裁"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的說法出來,就利用音韻學來講文字構造和通借了。
從錢大昕開始討論古紐,創立"古無輕唇、舌上"音的理論,直到曾運乾的《喻母古讀考》,研究古紐的穩步發展著。但是精神和講韻部的一樣:分類,和類與類之間的通轉。精神是越古的就越好。
總的看起來,這個時期的音韻學從給經學服務出發,到“小學”“蔚為大國”,音韻為《說文》作註腳結束,始終沒離開經學,因為“小學,所以通經”。清代經學最盛,所以講古韻講諧聲的真是百花齊放。裡頭也有毛奇齡(1623~1716)這樣專跟流行說法唱反調的人。古紐跟通經關係沒那麼直接,就比較冷落。這就是第2期的為經學作附庸的精神。第2期直到1940年左右才結束,可以叫“分類期”。在這一期里,音韻學從“自在”的變成“自為”的了。
第3期從清代陳澧作《切韻考》內·外篇開始。上期作者材料多、引書博,免不了有粗枝大葉的地方。陳澧開始就一部書──《廣韻》的反切作深入的研究。有多少聲類,多少韻類?聲類能分清、濁不能?四聲相承關係怎麼樣?以及字屬幾等?是開口還是合口?有一字多音的沒有……,等等。就各個方面作了細緻的研究。這就是徹底分析一批材料內部提供的信息。這跟印歐語史學里所謂一種語言內部的上溯大致相像。從這裡開始,方法可以說是相當科學化了。以後研究《切韻》音的人,每個人都下過這樣的工夫。
陳澧雖然沒見過《切韻》殘本,可是他先抓《切韻》音系是“一發中的”了。切韻上承上古音,下開現代音的局面,正是研究音韻學的核心資料。音韻學家許多人,各有貢獻。但是第一個找著正門的金鑰匙的是陳澧。推求上古音韻,解釋古方言的,討論古韻文的,調查現代方言的,都拿切韻音系作始發站。這個時期的高潮晚到20世紀50年代。這第3期可以叫“內析期”。
第 4期從20世紀30年代高本漢發表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開始。他的工作里用了一種新方法──印歐比較語史學的比較法。從各個方言現在讀音出發,加上外國譯音,像日本的吳音、漢音,越南朝鮮的漢字音,等等。他用比較法上溯,推求並且用音標記錄出所謂“7世紀長安音”,實際上是洛陽及其附近地區的通語音。高本漢的材料偏重西北。東南方言,如客家話,連第一手材料都沒有。偏巧在保存漢語語音古代面目方面,東南遠比別的方言重要。只看見北方話廣州話陽平吐氣,就把“並”定成【b‘】,雖經陸志韋、李榮二家糾正也堅決不接受。甚至於內部分析工作還不如陳澧仔細,竟把重紐現象抹殺。這些在歐美都讓好多人以訛傳訛,工作說不上完美。不過他帶來了新方法,運用了新材料。所以在運用歷史比較法和方言資料上他和陳澧成了“百世不祧之宗”。現在講音韻學的多數學者都在他們的流派裡頭。這個第4期和第3期一樣,還遠沒結束。第4期可以叫“旁征期”。